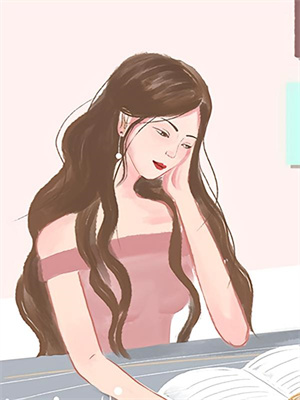简介
由著名作家“俐子花开”编写的《人间烟火悠长》,小说主人公是陈建国张玉兰,喜欢看年代类型小说的书友不要错过,人间烟火悠长小说已经写了89362字。
人间烟火悠长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1972-1974
日子像筒子楼公共水龙头里那永远拧不紧、滴滴答答漏下的水,不紧不慢地淌着,偶尔断流,偶尔又猛地喷射出一股带着铁锈味的激流,溅人一身冰凉。陈建国和张玉兰的婚姻生活,就在这十二平米的小单间里,在煤烟味、潮湿气、劣质烟草味、邻居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和永不缺席的家长里短中,正式拉开了厚重而斑驳的帷幕。
这幢红砖筒子楼是铁路局的家属宿舍,建于五十年代末,如今墙皮剥落,楼道幽暗,每一块斑驳都写着生活的磨损。十二平米,放下一张单人床(结婚时,建国找了段里的木工师傅,用废旧枕木和木板勉强加宽,拼成了双人床,一动就吱呀作响)、一张坑洼掉漆的旧办公桌(建国从段里淘汰物资里淘换来的)、一个装衣服的樟木箱(玉兰母亲留下的唯一像样的嫁妆),再加上墙角整齐垒起的蜂窝煤和一小堆引火用的刨花木屑,空间就被挤占得满满当当,转个身,胳膊肘都可能磕到冰冷的墙壁。唯一的“奢侈”品,是窗台上那个破陶盆里栽的几棵蒜苗,还有一盆玉兰精心伺候、叶子总是洗得翠绿的吊兰,它们是玉兰在匮乏日子里挤出的一点生机,一点不肯屈从灰暗的倔强绿意。
生活的第一课,是抢水。筒子楼每层只有一个公用水房,三个水龙头,却要伺候整整二十多户人家。早、中、晚三个时段,水龙头前永远排着蜿蜒的长龙。塑料桶、铁皮桶、搪瓷盆、铝锅碰撞得叮当响,抱怨声、催促声、招呼孩子声不绝于耳,那水流却时常细得像奄奄一息的溪流,甚至干脆罢工。水质也堪忧,时常泛着可疑的黄色,沉淀一会儿,桶底就是一层细沙。
玉兰通常天蒙蒙亮就拎着两只铁皮桶去排队,裹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呵着团团白气。她计算着时间,既要抢到水,又不能耽误给建国做早饭——他常常要赶早班车。建国要是跑夜车回来得早,也会挣扎着从短暂的睡眠中爬起来,混沌着双眼,接过水桶,沉默地加入那条困倦而焦躁的队伍。水房里永远湿漉漉、滑腻腻的,弥漫着肥皂泡、漂白粉、铁锈和人体油脂的混合气味,踩上去需要万分小心。邻居们一边机械地挪动脚步,一边交换着各种生存情报:副食店明天或许会来一批不要票的处理的蔫巴黄瓜,煤店这个月的蜂窝煤配额好像少了五块,传达室有谁家的汇款单,三车间老王家的儿子下乡插队时受了腿伤可能要办病退回城……声音在布满污渍的瓷砖墙壁上撞来撞去,嗡嗡作响,汇成一曲嘈杂刺耳的市井交响。抢到水,一天才算有了底气,家里的暖水瓶、搪瓷脸盆、做饭的锅才算有了内容。
第二课,是伺候那祖宗般的煤炉。冬天取暖、四季做饭,全靠墙角那个用砖头和黄泥巴糊起来的煤炉子。它脾气暴躁,难以捉摸。生火是每天清晨的一场战斗。先用废作业本或旧报纸引燃易燃的刨花、碎木屑,再小心翼翼地架上一两块珍贵的引火煤,拿着破蒲扇对着炉眼拼命扇风,等那点可怜的火苗终于舔着了引火煤,才能屏住呼吸,用火钳夹着正规的蜂窝煤,一块块小心地加上去。整个过程烟雾弥漫,催人泪下,稍有不慎,火苗“噗”地一声灭了,前功尽弃,只能黑着脸重新开始,心情也跟着一片灰暗。
建国是伺候煤炉的主力。他手稳,有耐心,也舍得力气捣鼓,似乎把在部队里保养武器的那份细致用在了这上面。但玉兰也很快被逼着学会了。那是1973年初夏,建国跑一趟长途临客,来回要三天。半夜,煤炉的火弱得只剩一点幽蓝的心子,眼看就要熄灭,屋里温度骤降。玉兰感到一阵寒意,也深知这炉火一旦灭了,明天一早的生火会是怎样的麻烦和烟熏火燎。她咬着牙,披衣起来。她学着建国的样子,跪在炉边,先用火钳轻轻捅了捅炉底,灰烬簌簌落下,然后小心地添上一小块新煤,对着炉眼笨拙地、小口小口地吹气,被倒烟呛得连连咳嗽,眼泪直流。汗珠从她的额角滑落。折腾了将近半小时,那微弱的火苗才终于不情不愿地重新旺了起来,橘红色的光映着她沾满煤灰、汗湿的脸颊和眼中被呛出来的泪花,也重新将一点微弱的暖意注入冰冷的房间。第二天下午建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看到炉火正旺,炉子上坐着一锅咕嘟冒气的粥,玉兰靠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捏着一块抹布,脸上残留着没洗净的黑道子。他没说话,放下行李,默默打来水,拧了热毛巾,极其轻柔地给她擦脸。玉兰惊醒,看到他眼中的血丝,只是笑了笑,说:“炉子没灭。”
1973年酷暑,玉兰怀孕的消息像一颗被小心翼翼捂着的种子,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小屋里悄然发芽,带来一种隐秘而巨大的喜悦,也让原本就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精打细算。建国黝黑的脸上,那惯常的严肃神情里,开始时不时地溜出一丝藏不住的、几乎是笨拙的笑意,走路时腰板似乎挺得更直了,但看着玉兰时,眼神里又多了几分不知所措的紧张和呵护。他跑车更勤了,休息时间也去帮人顶班、替同事值夜,就为了多挣那一点出车补助和加班费,多换几张珍贵的粮票、油票,好让玉兰能吃得好一点。
盛夏的筒子楼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闷热难当。公共厨房里弥散的不再是冬日里那点暖意融融的油烟,而是各种食物气味在高温下发酵、混合成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腻人浊气。玉兰的妊娠反应在这酷热中来得格外凶猛,闻不得半点油腥,常常端着碗,躲到相对通风却依旧燥热的楼梯拐角处,或者回到自己闷热的小屋,开着窗,就着一点咸菜和凉白开,艰难地吞咽几口饭了事。建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小小的煤油炉在夏日里更是煎熬,一点火,屋里温度陡增,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时不时给玉兰煮点清粥,额上的汗珠滴进锅里也浑然不觉。玉兰孕吐得厉害时,脸色苍白,伏在床边干呕,建国就笨拙地站在一旁,用那把破了边的蒲扇给她扇风,递上一杯晾凉了的、加了点宝贵白糖的开水,或者默默削一个蔫软的西红柿,切成小块喂给她,那一点酸甜,有时竟能奇迹般地压住翻涌的恶心。
营养是最大的问题。一切都要票证,一切都很稀缺。鸡蛋、肉、白糖,每一样都金贵无比。建国开始动用他所有的关系和门路。有时,他凌晨三四点才带着一身暑气和疲惫回来,蹑手蹑脚地,从怀里掏出个用湿毛巾裹着的小布包,里面有时是两个煮熟的鸡蛋,被体温捂得温热;有时是一小条难得一见、用油纸包着的黄瓜;甚至有一次,是一小包珍贵的绿豆,好让玉兰熬汤解暑。“快,吃了。”“煮点绿豆汤喝,去去火气。”他总是这样说,语气不容置疑。玉兰问哪来的,他就含糊地敷衍:“跟站里同事换的。”“跑车路过乡下,老乡塞的。”“你别管,用了就行。”后来玉兰才从别人口中零碎得知,他是用自己替别人顶夜班的“好处”——有时是对方塞给他的几支好烟,他舍不得抽攒起来;有时是人家匀给他的半块西瓜;甚至是用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去跟那些有点特殊门路的人换来的。她摸着那温热的鸡蛋或冰凉的黄瓜,看着建国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和眼下的乌青,喉咙像是被一团温热而酸涩的东西死死堵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把东西分成两半,固执地把一半塞进建国嘴里,逼着他一起吃下去。沉默中,那种相濡以沫的酸楚和温暖,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日子就在这抢水、生火、孕吐、期盼和无声的牺牲中,像楼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一样,由夏日的浓绿渐渐染上秋的黄。玉兰的肚子一天天隆起,像揣着一个越来越真实的希望。到了秋凉时分,晚上,两人挤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建国有时会小心翼翼地、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敬畏,把手掌轻轻覆在玉兰绷紧的肚皮上。第一次感受到那微弱却无比清晰的胎动,像小鱼吐泡,又像蝴蝶振翅,他像被电流击中一样猛地缩回手,瞪大了眼睛,黝黑的脸上满是惊奇和难以置信,像个第一次看见浩瀚星空的孩子。玉兰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拉过他的手,再次放在那个刚刚鼓起小包的地方。昏黄的15瓦灯泡下,两人头靠着头,屏息感受着那生命的律动,小小的房间里弥漫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的温馨和静默的狂喜。这一刻,所有的艰辛仿佛都被那小小的跳动温柔地踏碎了。
然而,筒子楼的生活,永远不可能只有温馨。隔墙的阴影无处不在,像角落里潮湿霉斑一样,无法忽视。
他们的隔壁,住着老钱夫妇。钱师傅是建国机务段里的同事,开蒸汽机车的,脾气跟他负责的那个铁疙瘩一样又硬又躁。钱师娘也是个直性子,嗓门洪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是家常便饭,争吵的导火索千奇百怪:水费好像多摊了一分钱,煤炉灰倒错了地方占了她家门口一点地,谁洗碗时不小心摔了一个有豁口的破碗,甚至是晚上睡觉谁多抢了一点被子。
争吵的声音毫无阻碍地穿透薄薄的、空心的隔墙,清晰地、尖锐地灌入建国和玉兰的小屋。
“……你个没良心的!我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跟着你吃没好吃穿没好穿,窝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放你娘的屁!老子一天到晚拉着一车皮的人,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你还有脸叫屈?”
“砰!”一声闷响,像是搪瓷盆狠狠摔在了地上,或者是什么东西砸在了门上。
“摔!你摔啊!有本事把我也摔死!这日子没法过了!”
接着是孩子受到惊吓的尖锐哭嚎,大人更加暴躁的咆哮,锅碗瓢盆更激烈的碰撞声,有时还夹杂着推搡扭打的声音……
每当这时,建国和玉兰就陷入一种无奈的沉默。建国通常会猛地停下手里正在看的业务书,或者修理的什么小物件,烦躁地皱紧眉头,狠狠吸一口劣质烟,烟雾在他紧锁的眉宇间缠绕,然后他翻个身,用后背对着墙壁,试图隔绝那噪音。玉兰则停下手里正在缝制的婴儿小衣服(那些衣服是用她和建国的旧衣服、用节省下来的布票买的白布染了色,一点点拼凑出来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布料,轻轻叹口气,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厌烦,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那些尖锐的、充满怨毒和绝望的字眼,像冰冷的针,一根根扎进这小小的、努力维持温暖的空间,也扎在人心上,提醒着他们生活最粗粝残酷的一面。
有一次吵得特别凶,从晚饭时间一直持续到深夜。骂声越来越高亢,伴随着清晰的耳光声和女人歇斯底里、近乎崩溃的哭喊尖叫,还有家具被猛烈撞击的声音。建国猛地从床上坐起身,脸色铁青,额上青筋跳动,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去。玉兰吓得心脏怦怦直跳,赶紧扑过去拉住他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建国!别去!求你了……别惹事……”
建国胸膛剧烈地起伏,像风箱一样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那面传来不堪声响的墙壁,仿佛要把它瞪穿。黑暗中,玉兰能感受到他手臂肌肉的僵硬和颤抖。僵持了漫长的十几秒,隔壁的哭骂声变成了呜咽和含糊的诅咒,建国才像被抽掉了力气一样,颓然地、重重地躺了回去,发出一声压抑的、沉重的叹息。黑暗中,他摸索着,找到了玉兰的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心滚烫,带着粗糙的薄茧和潮湿的汗意,力量大得几乎捏痛她。玉兰没有抽回手,反而回握住他,另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手背,像是在安抚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
他们没有说话。隔壁的战争似乎暂时休战,只剩下低低的、持续的啜泣声,像幽灵一样在楼道里游荡。但在这张狭窄的木板床上,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两只手紧紧交握着,汗湿相融,传递着无声的惊悸、安抚和一种深刻的默契。那是一种共同的抵御,抵御着近在咫尺的暴戾与不幸,抵御着生活随时可能显露的獠牙。他们像是狂风暴雨中两只紧紧依偎、羽毛凌乱的小鸟,用沉默的体温和心跳告诉对方: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起,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玉兰重新拿起那件快要完成的小衣服,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一针一线地缝着,针脚细密而整齐。碎布拼成的图案,虽然简陋,却透着一股认真的暖意。建国听着那细碎的、有节奏的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嘶啦——嘶啦——,听着隔壁渐渐低下去的呜咽,听着窗外远处传来火车进站或出站时悠长而空洞的汽笛声,还有那永恒不变的、轮毂撞击铁轨接缝发出的、规律而让人心悸的“哐当——哐当——”声,那声音仿佛碾过夜色,也碾过人心。他紧绷的神经在这混合的声响中,奇异地慢慢松弛下来。他侧过头,借着那一点微光,看着玉兰专注而柔和的侧影,看着她腹部巨大的、安静的弧线。那里孕育着他们的希望,一个他们拼命想要为其创造更好一点生活的未来。
筒子楼的日子,就是由这些碎片拼凑而成:清晨抢水时的匆忙与算计,生炉子时的烟熏火燎与耐心,公用水房里永远洗不完的衣物和闲言碎语,公共厕所刺鼻的气味和需要鼓足勇气才敢踏进去的尴尬,邻居家飘来的时好时坏的饭菜香气和永无休止的争吵,以及自家小屋里那一点点用热鸡蛋、白糖水、煤油炉和碎布片艰难守护的温暖与期盼。
197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煤炭供应紧张,每家的配额都减少了。屋里那点煤炉的热气,根本无法对抗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凛冽寒风。水房的水管冻住了,只能用暖水瓶里攒下的热水一点点去浇开,或者干脆去一公里外的单位开水房挑水。玉兰的孕期已进入后期,身体沉重,寒冷的天气让她行动更加不便,脚肿得厉害。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玉兰感到一阵紧过一阵的腹痛,她推醒身边刚入睡不久的建国,声音带着惊慌:“建国……我肚子……好像不太对劲……”建国瞬间清醒,摸黑拉开灯,看到玉兰苍白的脸色和紧蹙的眉头,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深更半夜,外面大雪封路,自行车都没法骑。他一把用厚厚的棉被裹紧玉兰,背起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冲进风雪里,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踉跄着往三站地外的铁路医院跑。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雪花迷住了眼睛。玉兰在他背上痛苦地呻吟,断断续续地安慰他:“建国……慢点……我没事……”建国咬着牙,汗水混着雪水从额头流进眼睛,涩得发痛,他不敢停,每一步都踩得无比沉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那三里路,仿佛比他开过的任何一条铁路线都要漫长、都要艰难。终于看到医院门口那盏昏暗的灯时,建国几乎虚脱,嗓子眼满是血腥味。
医生检查后,说是动了胎气,有早产风险,需要立即住院观察保胎。建国忙着办手续、交押金,又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恳求医生用最好的药(尽管他知道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好药”)。玉兰被推进了观察室,建国被拦在外面。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听着里面玉兰压抑的痛哼,看着窗外依旧肆虐的风雪,第一次感到一种彻骨的无力感。他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粗糙的砖墙硌着他的脊背。时间一分一秒都无比煎熬。他脑子里闪过无数可怕的念头,又强迫自己压下去。他不能想象失去玉兰或者孩子任何一个会怎样。
好在,经过一夜的输液和观察,玉兰的情况稳定了下来,宫缩逐渐平息。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加上寒冷刺激所致,嘱咐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建国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一点,但看着玉兰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依旧苍白,他的心又揪紧了。他在病床前守了整整两天两夜,困极了就在床边趴一会儿。玉兰醒来,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下巴上冒出的青黑胡茬,心疼不已,轻声说:“我没事了……吓着你了……回去歇歇吧,炉子别灭了……”建国摇摇头,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我就在这儿。”
这次突如其来的风波,花光了他们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积蓄,也让建国和玉兰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脆弱和为人父母即将到来的沉重责任。回到筒子楼,生活依旧,抢水、生炉子、算计票证,但气氛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建国包揽了所有重活,玉兰被严格限制活动,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床边,继续缝制那些小小的、用碎布拼成的衣物,每一针都缝进了担忧与希望。
隔壁的争吵依旧时不时爆发,但似乎不再那么具有穿透力了。建国和玉兰学会了更有效地屏蔽那些噪音,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内部那种共同的忧虑和期待所占据。他们的手在餐桌下、在床边、在黑暗中交握的次数更多了,一种更深的、共同承担命运的纽带在无声中变得更加牢固。
筒子楼依旧喧嚣、破败、拥挤不堪。但在这十二平米的方寸之地,在这片充满了煤烟、潮湿、噪音和他人不幸的堡垒里,陈建国和张玉兰,用他们的沉默、坚韧、和深藏在粗粝生活下的温柔爱意,一次次击退生活的寒意,像窗台上那盆蒜苗,顽强地向着稀薄的阳光,生长着,等待着那个最终将在下一章降临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