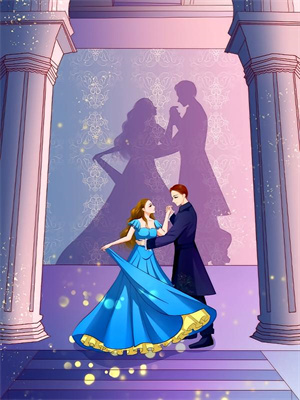简介
《武安君白起传》是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历史古代小说,作者“泛舟常江”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白起的精彩故事。本书目前已经连载,热爱阅读的你快来加入这场精彩的阅读盛宴吧!
武安君白起传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第一节:武师院中学剑艺
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3月5日,惊蛰,秦国郿邑(今陕西眉县)白家村西头武师院。
惊蛰的雷声刚滚过陇山,震得武师院的老槐树晃了晃,挂在枝桠上的沙袋还在摆——白起握着木剑,指节因用力泛白,刚被武师周仓用竹条抽过的手背,还带着点麻意,像被蚂蚁咬过。木剑是槐木削的,比他的胳膊还粗三寸,剑身上磨得发亮,是前几届学徒用剩下的,靠近剑柄的地方,还留着几道浅浅的刻痕,是前辈们练剑时蹭出来的。
沙袋是粗麻布缝的,里面装着粟壳和沙土,被劈得有些变形,边角露出点淡黄色的粟壳,风一吹,飘出点细碎的壳子。周仓站在对面,穿着褐色短褐,腰间系着根磨得发亮的牛皮绳,手里拿着根竹条,竹条上还沾着点露水,是早上从院角的艾草丛里折的。“劈剑要沉肩,别用胳膊劲!”周仓的声音带着点沙哑,是当年在河西战场喊口令喊伤的,“你看这沙袋,要劈在正中间,才能练出准头——将来战场上,你劈不准魏兵的甲缝,就得被魏兵的长剑砍中!”
白起咬着牙,把短褐的袖子往上捋了捋,露出细瘦却结实的胳膊,调整姿势,沉下肩膀,再一次把木剑劈向沙袋。“嘭”的一声闷响,沙袋晃得更厉害,粟壳的香气混着尘土的味道飘过来,钻进鼻腔,他的手背又疼了,却没敢吭声——刚才同乡二狗就是因为喊疼,被周仓多抽了两下,竹条落在身上的声音,现在想起来还发怵。
二狗比白起高半个头,却瘦得像根粟杆,握着木剑的手一直在抖,剑身在他手里晃悠悠的,连沙袋都碰不到。他劈了没几下,就放下木剑,揉着胳膊,胳膊上的肌肉都绷得发僵:“周师傅,太累了,歇会儿吧!这木剑比挑水的扁担还沉,练了也没用,将来从军不一定能用上——我爹说,当兵靠的是力气,不是耍剑花。”
周仓走过去,竹条轻轻敲了敲二狗的木剑,发出“笃笃”的声:“没用?当年我在河西,要是没练过剑,早被魏兵砍了胳膊!”他撩起短褐的下摆,露出左腿上一道长长的疤痕,疤痕泛着淡粉色,是当年被魏兵的剑划的,“这道疤,就是因为我剑没练熟,没挡住魏兵的劈砍。你们现在练的每一下,都是将来战场上的活命本事,不是耍剑花。”
他转头看向白起,眼里带着点期许:“白起,你说,该不该歇?”
白起放下木剑,手背的红印还很明显,像抹了层胭脂,他走到二狗身边,看着他发颤的手:“二狗,练剑能保命,将来从军,咱是五人一伍,你要是剑练不好,不仅自己会受伤,还会拖同伍的后腿。周师傅说,秦军的什伍制,一人不行,全伍受罚,咱不能当软蛋,让村里人笑话。”
二狗撇了撇嘴,却还是拿起木剑,剑身在他手里还是有点晃:“行吧,听你的。不过我可没你能扛,练会儿就得歇,你别催我。”
周仓点点头,眼里露出点赞许,转身从墙角拿起一块木片——木片是杨木做的,很轻,上面用炭笔画着简单的剑招,一道是“劈”,一道是“刺”,线条歪歪扭扭,是周仓自己画的。“今天教你们这两招,”他把木片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战场上最管用的——劈能断敌兵的盾,刺能穿敌兵的甲缝。你们记住,劈要沉肩送腰,刺要直臂送力,别偷工减料。”
白起凑过去,盯着木片上的剑招,手指在上面跟着画,炭粉沾在指尖,黑乎乎的:“周师傅,劈的时候,剑尖要朝下多少?刺的时候,腰要送多远,才能刚好穿甲缝?”
“问得好!”周仓笑了,拿起木剑,在空地里示范了一遍,木剑划过空气,发出“呼”的声,“劈的时候,剑尖朝下三成,太陡会劈空,太缓会被盾弹开;刺的时候,腰送半尺,刚好能穿魏兵的皮甲缝——当年我在河西,就是用这招,刺中了一个魏兵的甲缝,救了同伍的兄弟。”
太阳慢慢升高,霜气散了,武师院的土地被晒得有些暖,地上留下了一排排木剑劈过的痕迹,深浅不一。白起练得最认真,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滴在土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短褐的后背已经被汗透了,贴在身上,有点黏腻。二狗练了一会儿,又开始偷懒,靠在槐树上喘气,手还在揉胳膊,脸上满是疲惫。
白起走过去,从怀里掏出一块麦饼——是早上娘给的,用粗布包着,还带着点温乎气,麦饼上撒了点盐,是娘特意放的,说练剑耗力气,要补补盐。“吃点吧,补充力气。”他把麦饼递给二狗,“周师傅说,明天要教举石,要是力气不够,举不起来,还得被竹条抽——你现在多吃点,明天有力气举石。”
二狗接过麦饼,咬了一大口,麦饼的麦香混着盐味,在嘴里散开,他含糊地说:“知道了,谢谢你啊白起。我就是有点怕疼,不是不想练——我娘说,我从小就怕疼,连扎针都哭。”
“怕疼也得练,”白起坐在他旁边,也咬了口麦饼,麦饼的碎屑掉在腿上,他赶紧用手接住,“将来从军,战场上的刀箭可比竹条疼多了,要是现在不练,到时候连挡都挡不住,只会更疼。我娘也怕我疼,可她还是让我来练剑,说为了活命,疼也得扛着。”
二狗点点头,没再说话,三口两口吃完麦饼,拿起木剑又开始练,这次手不怎么抖了,木剑也能劈到沙袋的中间。周仓看着他们,嘴角露出点笑,转身从屋里拿出一把旧铜剑,放在院中的石桌上——剑鞘是黑色的,有些地方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铜色,像老人脸上的斑,剑鞘上还有一道裂痕,是当年被魏兵的剑砍的,裂痕里还沾着点暗红色的锈迹。
“这把剑,是我当年在河西战场上捡的,”周仓摸着剑鞘,声音有些沉,像是在回忆往事,“原主是个秦军伍长,姓赵,为了护粮道,被三个魏兵围着砍,最后力竭而死。他要是剑练得再熟点,说不定能活下来,能回家见他的老娘。”
白起盯着铜剑,眼睛发亮,像看到了宝贝,他慢慢走过去,手指轻轻碰了碰剑鞘,铜鞘的凉意透过指尖传来,带着点金属的腥气:“周师傅,将来我能用上这样的剑吗?我要是立了军功,也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铜剑吗?”
“只要你好好练,将来从军立了军功,别说铜剑,就是铁剑也能有!”周仓拍了拍他的肩,手掌的老茧蹭着白起的短褐,“秦军的军功爵制,斩首一级就能获公士爵,赏钱五千,布二匹,还有好兵器。你要是能练出真本事,将来肯定能用上比这更好的剑,能让你娘为你骄傲。”
白起握紧了手里的木剑,木剑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练剑,将来从军立军功,用上真正的铜剑,像周师傅说的赵伍长一样,保护同伍的人,不被敌人砍死,还要让娘为他骄傲,让白家村的人都知道,他白起不是软蛋。
夕阳西下的时候,周仓检查了每个人的剑招,只有白起练得最标准,劈能中沙袋正中,刺能穿沙袋上的草绳。“白起,你留下,”周仓说,手里还拿着那把旧铜剑,“我再教你个小技巧,劈剑的时候,手腕稍微转一下,能更容易劈断敌人的兵器——当年赵伍长就是没会这招,剑才被魏兵砍断的。”
白起留下来,跟着周仓学技巧,直到月亮升起来,银辉洒在武师院的地上,像铺了层白霜,才拿着木剑回家。路上,他还在比划着剑招,月光照在他的短褐上,像撒了层银粉,木剑在手里挥着,带起阵阵风。他想起周师傅的铜剑,想起军功爵,想起娘期待的眼神,心里充满了干劲——他要快点长大,快点学好武艺,将来当一名好兵,让爹娘骄傲,让白家村骄傲。
第二节:老卒帐内话沙场
秦惠文王十六年(前322年)9月8日,白露,秦国郿邑(今陕西眉县)北坡老卒王有家帐前。
白露的霜气沾在白起的短褐上,像撒了层细盐,摸上去凉丝丝的,钻进衣领里,让他打了个寒颤。他蹲在老卒王有的帐前,手里攥着根木片,木片上用炭笔画着简单的剑招——是昨天周师傅教的“刺”,他还没练熟,剑总是刺不准,想让王有指点指点,王有当年在河西打过仗,懂的比周师傅还多。
王有的帐是粗麻布搭的,四角用木桩固定在地上,帐顶还沾着点枯草,是去年冬天刮大风时刮上去的。帐旁边堆着些粟草,是用来喂牲口的,王有养了一头老黄牛,平时用来耕地,现在正拴在帐后的槐树上,慢悠悠地嚼着草。帐前的陶灶上,还放着一个陶锅,锅里的粟粥已经凉了,却还飘着点米香,是王奶奶早上煮的,王有没喝完。
王有坐在帐前的木凳上,木凳是槐木做的,凳面被磨得发亮,他穿着件灰色的旧短褐,短褐的袖口还打着补丁,是王奶奶缝的。他手里拿着个陶碗,碗里盛着米酒,是自家酿的,度数浅,带着点甜香,他喝了一口,咂咂嘴,脸上露出点满足:“白起,你昨天问的‘刺’招,哪儿没弄懂?是送腰不够,还是直臂不准?”
白起赶紧把木片递过去,木片上的炭笔道已经有些模糊:“王爷爷,我刺的时候,总觉得力用不到剑尖上,刺不深,周师傅说我送腰不够,可我觉得已经送得够远了,是不是哪里错了?”
王有接过木片,放在腿上,指着上面的剑招:“你看,刺的时候,不光要送腰,还要蹬腿,脚底下要稳,力从腿上起,经过腰,传到胳膊,最后到剑尖,这样才能刺得深。当年我在河西,就是因为蹬腿没蹬稳,刺魏兵的时候,只刺进去半寸,没伤到要害,差点被魏兵反砍一刀。”
白起点点头,站起来,按照王有的说的,比划了一下,脚蹬在地上,腰往前送,胳膊伸直,果然觉得力能传到剑尖了:“谢谢王爷爷,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这么练。”
“这就对了,”王有笑了,又喝了口米酒,“你这娃,心思细,学东西快,比当年的我强多了。我当年学刺招,学了半个月才学会,你才学一天,就差不多懂了。”他放下陶碗,从怀里掏出一块铜剑残片,残片有巴掌大,上面还带着锈迹,边缘参差不齐,是当年他在河西战场上捡的,“你看这个,是魏兵的剑残片,魏兵的剑比咱秦军的长半尺,还锋利,要是一对一,咱秦军的卒子,还真不一定能打过。”
白起捡起铜剑残片,指尖蹭过锈迹,带着点粗糙的凉意,还有种金属的腥气,他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闻到点淡淡的土味:“王爷爷,魏兵的剑这么厉害,当年河西之战,咱秦军咋赢的?是不是靠人多?我听村里的人说,当年秦军派了十万人,魏兵才五万人。”
“靠人多也不行,”王有摇了摇头,把铜剑残片拿回来,小心地放在怀里,“得靠阵形,靠协同。当年河西之战,魏兵的‘魏武卒’冲过来,个个都拿着长剑,穿着厚甲,看着吓人,可咱秦军列着‘科头锐士’阵,五人一组,一人劈剑,一人举盾,一人射箭,两人护侧翼,魏兵的长剑再厉害,也冲不破咱的阵。”
白起的眼睛瞪得溜圆,像看到了稀奇事:“王爷爷,啥是‘五人一组’?为啥不三人一组,或者十人一组?三人一组人少,灵活,十人一组人多,厉害,五人一组不多不少,是不是有啥讲究?”
王有笑了,从地上拿起五根木片,摆成一个小圈,木片之间的距离差不多:“这就是‘伍’,秦军的什伍制,五人为伍,设伍长;十人为什,设什长。五人一组,能互相照应——你劈剑,我护你后背,不让敌兵砍你;我射箭,你帮我挡箭,不让敌兵射我。要是三人一组,人太少,护不过来,容易被敌兵包围;十人一组,人太多,转不开,容易乱,阵形一乱,就容易被敌兵冲散。”
白起跟着王有的样子,用木片摆了个“伍”字,却摆得歪歪扭扭,木片之间的距离有的近有的远:“王爷爷,我摆的咋这么乱?是不是我没摆好?”
“慢慢来,别急,”王有耐心地教他,“伍阵的距离,要根据兵器来定,举盾的人离劈剑的人要近,差不多一尺远,这样能刚好挡住劈剑的人;射箭的人要在后面,离前面的人三尺远,这样能射箭,又不影响前面的人。你再试试,按照这个距离摆。”
白起按照王有的说的,重新摆了一遍,这次整齐多了:“王爷爷,那要是伍长死了咋办?剩下的人没人指挥,不就乱了吗?”
“伍长死了,就由最厉害的人当临时伍长,继续作战,”王有指着中间的木片,“秦军的规矩,什伍相保,一人逃,全伍罚;一人立功,全伍有赏。所以没人敢逃,也没人敢偷懒,都得拼尽全力,就算伍长死了,也能继续打。当年我在河西,我们伍的伍长就死了,我因为剑练得好,就当了临时伍长,带着兄弟们继续护粮道,最后还立了军功。”
正说着,帐外传来脚步声,是村里的孩子狗蛋,他今年十岁,比白起小六岁,手里拿着个陶盆,盆里装着粟米,粟米是刚碾的,还带着点糠皮:“王爷爷,我娘让我给您送点粟米,说您家的粟米快吃完了,让您先吃着,等秋收了再还。”
狗蛋放下陶盆,看到白起手里的木片,好奇地问:“白起哥,你在摆啥?是不是在玩打仗?我也想玩,带我一个呗!”
“不是玩,是学秦军的伍阵,”白起说,把木片往旁边挪了挪,给狗蛋让了个位置,“王爷爷说,五人一组,能打胜仗,将来从军,就得靠伍阵,不是玩。”
狗蛋撇了撇嘴,坐在地上,拿起一根木片,在手里晃着:“打仗有啥好的?我爹说,打仗会死人,他才不当兵呢!我爹还说,要是当了兵,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就没人给我买糖吃了。”
王有的脸沉了下来,语气也严肃了:“狗蛋,你这话就错了。咱秦人,男丁二十岁傅籍从军,是本分,是责任。要是没人当兵,魏兵、韩兵就会打过来,抢咱的粟米,烧咱的房子,到时候你娘的粟米,你也吃不上,你爹也没钱给你买糖吃。当年我要是不当兵,河西就丢了,咱郿邑说不定就被魏兵占了,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吃糖?”
狗蛋低下头,没敢说话,手里的木片也不晃了,眼睛红红的,像是要哭。白起看着狗蛋,拍了拍他的肩:“狗蛋,别害怕,当兵能立军功,赏钱赏田,还能保护家里人。王爷爷说,当年他立了军功,赏了两亩田,不然现在哪有粟米给你娘换布?将来你长大了,也当兵,立军功,给你娘赏田,让你娘不用再织布到半夜。”
狗蛋抬起头,眼里有点亮,看着王有:“王爷爷,当兵真的能赏田吗?赏了田,就能种很多粟米,就能换很多糖吗?”
“当然能!”王有笑了,摸了摸狗蛋的头,“只要你好好练本事,将来从军立军功,别说赏田,还能赏钱,赏布,让你娘过上好日子。你看白起,现在就好好练剑,将来肯定能立军功,你也要向他学习。”
狗蛋点点头,拿起木片,学着白起的样子摆伍阵:“我知道了,将来我也要好好练本事,当兵立军功,给我娘赏田。”
太阳渐渐落山,霜气更重了,帐前的陶锅已经凉透了,粟粥的香气也散了。白起要回家了,王有把那块铜剑残片递给她:“这个你拿着,是当年魏兵的剑残片,你看着它,就知道魏兵的剑有多硬,也知道咱秦军的阵有多厉害。将来你练剑累了,就看看它,想想河西之战的兄弟们,就有干劲了。”
白起接过残片,小心地放进怀里,对着王有躬身:“谢谢王爷爷,我明天还来听您讲战场的事,还来学伍阵。”
走在回家的路上,白起摸着怀里的铜剑残片,心里想着王有说的什伍制,想着军功爵,想着河西之战的阵形。月光照在土路上,像铺了层白霜,他仿佛看到了秦军列着伍阵,举着长戟,冲向魏兵,铜剑的寒光在月光下闪着,像星星一样,魏兵的长剑再厉害,也冲不破秦军的阵,最后只能被秦军打败。
回到家,娘正在灶间煮粟粥,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粟粥的香气飘出来,混着草木灰的味道,很暖和。爹在院里劈柴,斧头是铁打的,刃口磨得很亮,劈在木头上“哐哐”响,木柴被劈成一块块的,堆在墙角。
白起跑过去,把铜剑残片拿给爹看:“爹,这是王爷爷给我的,魏兵的剑残片。王爷爷说,五人一组能打胜仗,斩首一级能获公士爵,赏钱五千,布二匹,将来我从军,也要立军功,赏钱赏田,让您和娘过上好日子。”
白老栓放下斧头,拿起残片,放在手里看了看,指尖蹭过锈迹:“这残片,我认识,当年河西之战,我也见过这样的剑。王有说得对,学本事、学阵形,将来从军才能立军功。你好好跟着周师傅练剑,跟着王有学阵形,将来肯定比爹强,爹当年只立了个小功,没赏多少田,你将来肯定能赏很多田。”
白起点点头,走进灶间,帮娘烧火,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暖暖的。他看着娘的手,正在搅拌陶锅里的粟粥,手背上满是老茧,是常年织布、做饭留下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将来当一名最厉害的秦军士兵,立最大的军功,让爹娘过上好日子,让娘不用再织布到半夜,让爹不用再劈柴到天黑。
第三节:郿邑郊野观演武
秦惠文王十九年(前319年)5月12日,立夏,秦国郿邑(今陕西眉县)东郊秦军演武场。
立夏的太阳毒得很,像个大火球,烤得演武场的土地发烫,脚踩上去,能感觉到热气从鞋底往上冒,顺着裤腿往上窜,让人浑身发燥。秦军的演武场在东郊的高地上,地势平坦,周围围着木栅栏,栅栏是槐木做的,有些地方已经开裂,是常年风吹日晒造成的。栅栏外,站着不少村里的人,老的少的都有,都是来看秦军操练的——郿邑是秦国的军事重镇,城西就驻着秦军的校尉部,每月初一、十五,秦军都会在这里操练,每次操练,都有不少人来看,想看看秦军的本事,也想听听战场的消息。
白起挤在人群前面,个子比去年高了不少,已经能清楚地看到演武场里的景象。他手里拿着个布包,是娘用粗布缝的,里面装着两块麦饼和一个水囊,麦饼是早上娘烙的,还带着点油香,水囊里装的是井水,是早上刚打的,还带着点凉意。他今天特意起得早,就是为了占个好位置,能看清秦军的操练,尤其是伍阵和变阵,王有说过,秦军的演武场操练,比他讲的还清楚,还能看到实际的阵形变化。
演武场里,秦军士兵已经列好了队,穿着褐色皮甲,皮甲是用牛皮做的,边缘磨得有些发白,甲片之间的皮绳有些松脱,却还很结实。士兵们手里拿着长戟或铜剑,长戟的木杆是槐木做的,上面还带着点木纹,戟尖闪着冷光,有一尺多长;铜剑的剑鞘是黑色的,挂在腰间,随着士兵的动作轻轻晃动。什长站在队伍前面,手里拿着令旗,令旗是红色的,上面绣着个“秦”字,风一吹,令旗“哗啦啦”响。
“立阵!”什长的口令声传来,声音洪亮,震得人耳朵发麻,士兵们立刻停下脚步,排成整齐的横队,每五人一组,之间的距离刚好能挥戟,不多不少,正是王有说的“伍阵”。前面的士兵举着盾,盾牌是皮做的,里面衬着木板,能挡箭和滚石;中间的士兵举着长戟,戟尖朝前;后面的士兵背着弓箭,箭囊挂在肩上,里面装着十几支箭。
白起的眼睛瞪得溜圆,手指在布包上画着阵形,布包上沾了点尘土,画出来的阵形歪歪扭扭,却能看出个大概:“王爷爷,您看,他们真的是五人一组!中间的人举戟,两边的人举盾,后面的人射箭,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太厉害了!”
王有站在白起旁边,手里拿着个拐杖,是当年腿伤留下的后遗症,阴雨天就会疼,今天天气好,却也得拄着。他眯着眼睛,看着演武场,嘴角露出点笑:“没错,这就是伍阵的基础阵形。你看,前面的伍是‘前拒’,负责冲锋,要是敌兵来攻,就先冲上去,打乱敌兵的阵形;后面的伍是‘后拒’,负责掩护,要是前拒的人受伤了,就上去替换;两边的伍是‘侧翼’,负责防守,不让敌兵从侧面冲过来。这样不管敌兵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应对,不会乱。”
白起指着演武场左侧的一队士兵,那队士兵站在后面,没跟前面的队伍一起,手里拿着长戟,却没举起来:“王爷爷,那队士兵为啥站在后面,不跟前面的一起?是不是偷懒?还是他们是新来的,还不会操练?”
“不是偷懒,也不是新来的,那是‘预备队’,”王有说,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打仗的时候,前面的士兵累了,或者伤亡了,预备队就顶上,不让阵形出现缺口;要是前面的阵被冲开,预备队也能补上,不让敌兵趁虚而入。当年河西之战,魏兵冲开了咱前面的阵,就是预备队补上,才没让魏兵冲进来,没让粮道被断。要是没有预备队,粮道一断,咱秦军就没吃的了,不用打,就输了。”
正说着,演武场里的鼓声响起,“咚咚咚”的,很急促,像打在人的心上——是进攻的信号。什长挥动令旗,红色的令旗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前面的“前拒”伍立刻举着长戟,朝着前面的木靶冲去,嘴里喊着“杀!”,喊叫声传来,震得演武场的土地都在微微发颤。
木靶是用木头做的,有半人高,上面画着魏兵的样子,穿着厚甲,拿着长剑,画得很逼真。士兵们的长戟刺在木靶上,“噗”的一声,有的刺中胸口,有的刺中喉咙,都很准,没有刺偏的。白起看得入了神,手里的布包都忘了攥,布包从手里滑下来,掉在地上,他都没察觉,直到旁边的虎子碰了他一下,才回过神来。
“白起,你看那个什长,长得真高,比旁边的士兵高半个头,肯定很能打!”虎子是白起的同乡,比白起小两岁,手里拿着个糖葫芦,是他爹给买的,一边吃一边说,指着演武场里的什长。
白起捡起布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摇摇头:“不一定长得高就厉害,王爷爷说,打仗靠的是阵形和协同,不是单个厉害。你看,那个什长虽然高,要是没有后面的伍掩护,魏兵从侧翼冲过来,他一个人也打不过五个魏兵,照样会被砍死。当年河西之战,有个魏兵长得很高,力气也大,一个人杀了咱两个卒子,结果被咱的伍阵围起来,五个人一起上,他再厉害,也挡不住五把长戟,最后还是被斩首了。”
虎子撇了撇嘴,咬了口糖葫芦,糖渣掉在衣服上:“你就知道说,你又没打过仗,咋知道这么多?说不定那个什长就是很厉害,能一个打五个。”
“我听王爷爷讲过河西之战,还学过伍阵,王爷爷当年在战场上亲眼见过,还立了军功,他说的肯定没错,”白起说,“王爷爷说,单个再厉害,也打不过五个人;五个人再厉害,也打不过一个阵。所以秦军练阵形,比练单个本事还重要,要是阵形乱了,再厉害的人也没用。”
王有笑着说:“白起说得对。当年我在河西,就见过一个魏兵,力气很大,能举五十斤的石墩,剑也练得好,一个人杀了咱两个卒子,可他太骄傲了,冲得太靠前,脱离了自己的阵形,被咱的伍阵围起来,五个人一起上,他的剑再厉害,也挡不住五把长戟,最后还是被斩首了,他的剑也被咱捡了,就是我给白起看的那块残片。”
虎子听得入了神,忘了吃糖葫芦,眼睛盯着演武场,嘴里念叨着:“原来阵形这么厉害,我将来从军,也要学阵形,不做单个厉害的人,要做阵形里厉害的人。”
演武场里,进攻的信号停了,换成了防御的信号,鼓声变得缓慢,“咚——咚——咚——”的。士兵们立刻转过身,举着盾牌,形成一道盾墙,盾牌和盾牌之间靠得很紧,没有缝隙,后面的士兵举着长戟,从盾牌的缝隙里伸出去,对着前面的“敌兵”(其他队的士兵),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这是防御阵,”王有说,手指着演武场,“要是敌兵冲锋,就用盾墙挡住,不让敌兵冲过来,后面的长戟刺敌兵,敌兵冲不过来,还会被刺死,只能退回去。当年韩兵冲咱的阵,就是用的这招,韩兵死了不少,也没冲过来,最后只能投降,把城池让给咱秦军。”
白起指着盾墙的缝隙,缝隙很小,只能伸过长戟的尖:“王爷爷,那缝隙会不会太大?敌兵的箭能射进来吧?要是敌兵射箭,从缝隙里射进来,不就射中后面的士兵了吗?”
“不会,你看,盾牌之间的缝隙,刚好能伸过长戟,却射不进箭,”王有说,“这是秦军的规矩,盾牌要靠紧,缝隙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箭能进来,射中后面的士兵;太小,长戟伸不出去,刺不到敌兵。这些都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来的,错一点都不行,错了就会死人,就会输仗。当年我在河西,有个伍就是因为盾牌之间的缝隙太大,被魏兵的箭射进来,射死了两个士兵,差点让魏兵冲进来,最后还是预备队补上,才没出事。”
太阳升到头顶,阳光更毒了,演武场的土地被晒得发白,士兵们的皮甲都被汗透了,贴在身上,却还站得很直,没有一个人偷懒。操练停了,士兵们开始休息,有的坐在地上,拿出麦饼啃着;有的靠在栅栏边,喝水聊天;还有的互相检查装备,看看长戟有没有松动,盾牌有没有破损。
白起也拿出布包里的麦饼,递给王有一块:“王爷爷,您吃点麦饼,刚做的,还软乎,我娘放了点盐,好吃。”
王有接过麦饼,咬了一口,麦饼的麦香混着盐味,在嘴里散开,很美味:“好吃,比我家的麦饼软,你娘的手艺真好。白起,你今天看了操练,有啥想法?是不是觉得秦军很厉害?将来从军,有没有信心立军功?”
“我觉得,秦军的阵形真厉害,五人一组,协同作战,比单个练剑管用,”白起说,咬了口麦饼,“将来我从军,一定要学好阵形,跟同伍的人好好配合,互相照应,不拖后腿,立军功,赏钱赏田,让您和我爹娘都为我骄傲。”
“好样的,”王有说,拍了拍白起的肩,“不过你要记住,阵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战场上的情况,跟演武场不一样,敌兵不会按你想的来,不会乖乖地从前面冲过来,可能会从侧面冲,可能会绕到后面,所以还要会变阵,根据敌兵的情况,改变阵形,这样才能打赢。比如敌兵从侧翼来,就要把‘前拒’伍调到侧翼,变成‘侧翼拒’,把‘侧翼’伍调到前面,变成‘前拒’,这样才能挡住敌兵,不让敌兵冲进来。这叫‘料敌合变’,是最厉害的本事,学会了这个,才能当伍长、什长,甚至校尉。”
白起点点头,把王有的话记在心里,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料敌合变,我记住了。王爷爷,您当年在河西,变过阵吗?是不是很难?”
“变过,当然变过,”王有说,眼里带着点回忆,“当年魏兵从侧翼冲过来,校尉就让咱把‘前拒’伍调到侧翼,挡住魏兵,把‘侧翼’伍调到前面,继续进攻,最后才打赢的。变阵不难,只要练熟了,知道敌兵从哪里来,就把对应的伍调过去,就能挡住敌兵。所以你不光要学阵形,还要学变阵,不然到了战场,敌兵一变方向,你就慌了,阵形一乱,就输了。”
操练又开始了,这次是模拟敌兵从侧翼进攻,士兵们立刻变阵,动作很快,没有一点慌乱。“前拒”伍快速跑到侧翼,举着盾牌和长戟,挡住“敌兵”;“侧翼”伍跑到前面,举着长戟,继续进攻“敌兵”的正面;预备队留在后面,随时准备补上。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豹子,灵活又勇猛。
白起看得眼睛都不眨,手里的麦饼忘了吃,直到娘来找他,才知道已经到了下午,太阳都开始往西斜了。“白起,该回家了,你爹还等着吃饭呢!饭都快凉了,你娘煮了你爱吃的粟粥,还有鸡蛋。”娘的声音传来,手里拿着个布巾,走到白起身边,给白起擦了擦额头的汗,布巾沾了汗,变得湿湿的。
白起跟着娘,回头望了望演武场,士兵们还在操练,阵形变换得很快,像一群灵活的豹子。他心里想着“料敌合变”,想着伍阵,想着长戟,觉得今天学到的,比练一个月剑还多,比听王爷爷讲十次河西之战还清楚。
走在回家的路上,娘问他:“今天看操练,有啥感想?是不是觉得当兵很辛苦?要是觉得辛苦,咱就不学了,在家种庄稼,也能过日子。”
“不辛苦,”白起说,眼里带着点坚定,“当兵能保护家里人,还能立军功,赏钱赏田,让您和爹过上好日子。娘,将来我从军,一定要立军功,给您买新短褐,给爹买新斧头,还要赏田,让咱家的粟米吃不完,让您不用再织布到半夜,让爹不用再劈柴到天黑。”
娘笑了,摸了摸他的头,眼里带着点欣慰:“好,娘等着。不过你要先好好学本事,跟着周师傅练剑,跟着王爷爷学阵形,将来才能立军功,才能当一个好兵,一个让爹娘骄傲的兵。”
白起点点头,心里充满了干劲。他知道,离他从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要抓紧时间,学好本事,将来在战场上,做一名最厉害的秦军士兵,让爹娘骄傲,让白家村骄傲,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骄傲。
第四节:木片推演什伍制
秦惠文王二十一年(前317年)12月8日,冬至,秦国郿邑(今陕西眉县)白家村白起家院角。
冬至的太阳斜斜地照在院角,带着点微弱的暖意,像一层薄纱,盖在地上。白起蹲在院角的粟囤旁,粟囤是用荆条编的,里面装满了粟米,囤顶盖着厚厚的茅草,防止受潮。他手里拿着一堆木片,木片是他用槐木削的,有大有小,大的代表什长,比小的木片长一寸,上面画着个“什”字;小的代表伍卒,上面还画着简单的符号——“盾”代表举盾的卒子,“戟”代表举戟的卒子,“箭”代表射箭的卒子,符号是用炭笔画的,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了,是他反复推演蹭的。
今天是冬至,秦地的习俗,要吃粟粥,还要祭祖,祈求先祖保佑来年丰收,家人平安。爹娘在屋里忙着煮粟粥、准备祭品,祭品有粟米、麦饼、还有一块肉干——是昨天赶集买的,平时舍不得吃,只有过节或祭祖的时候才拿出来。白起趁空,就在院角推演秦军的什伍制——这是他跟王有学的,已经学了快一年,却总觉得还有地方没弄懂,比如什伍之间的配合,怎么变阵才能更快,才能更有效地挡住敌兵。
“伍长在前,举戟,负责进攻;左右各一人,举盾,负责防守,挡住敌兵的剑和箭;后面两人,一人射箭,负责远程攻击,一人护箭手,负责保护射箭的人,不让敌兵靠近,”白起嘴里念叨着,把木片摆成一个伍阵,伍阵很整齐,木片之间的距离刚刚好,“什长在伍阵后面,指挥两个伍,左边伍负责左翼,防止敌兵从左边冲过来;右边伍负责右翼,防止敌兵从右边冲过来;中间留一条通道,让预备队走,要是哪个伍需要帮忙,预备队就能从通道过去,很快补上……”
摆着摆着,他皱起了眉,手指停在右边的伍上——右边的伍摆得太靠外,离左边的伍太远,中间的通道太宽,要是敌兵从中间冲过来,两个伍来不及会合,通道就会被敌兵占领,阵形就会被冲散,到时候就会乱;他把右边的伍往左边挪了挪,通道变窄了,却又觉得离左翼太近,敌兵从右翼冲过来,右边的伍离得太近,来不及调整,挡不住敌兵,右翼就会被突破,整个阵形还是会乱。
“咋弄啊?”白起蹲在那儿,盯着木片半天没动,手指在地上画着“什”字,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地上的土都被蹭松了,指尖沾了土,黑乎乎的,也没弄明白,到底该怎么摆,才能既挡住中间的敌兵,又挡住侧翼的敌兵。
“白起,在干啥呢?娘煮好粟粥了,快来吃!再不吃,粥就凉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屋里传来娘的声音,还带着点粟粥的香气,飘到院角,钻进白起的鼻腔,让他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
“娘,我再摆会儿,弄明白这个什阵就来!马上就好,您先吃,不用等我!”白起喊道,手里的木片又挪了挪,把右边的伍再往左边挪了一点,通道更窄了,却还是觉得不对,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娘走进院,手里拿着个陶碗,碗里盛着粟粥,还冒着热气,她看到白起手里的木片,笑着走过去,蹲在白起旁边:“又在推演什伍制呢?王爷爷不是教过你吗?咋还没弄明白?是不是遇到难题了?跟娘说说,娘虽然不懂,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娘,我觉得两个伍的距离不好掌握,太远了怕中间被冲,太近了怕侧翼被攻,我咋摆都不对,”白起说,语气里带着点沮丧,“王爷爷说,当年河西之战,什伍的距离刚好,可我就是摆不好,是不是我太笨了?”
娘放下陶碗,拿起一块木片,木片上画着“盾”的符号,她放在手里看了看:“你别光盯着木片,想想你练剑的时候,周师傅咋教你的?劈剑要沉肩,刺剑要送腰,都是有规矩的,不是随便劈随便刺的。什伍的距离,肯定也有规矩,不是随便摆的,你问问王爷爷,不就知道了?王爷爷当年在战场上用过什伍制,肯定知道怎么摆,怎么调整。”
白起眼睛一亮,像看到了希望:“对呀,我可以去问王爷爷!娘,我吃完粟粥,就去王爷爷家,问问他什伍的距离咋定,怎么摆才能既挡住中间,又挡住侧翼。王爷爷肯定知道,他最懂什伍制了。”
“好,先吃粟粥,凉了就不好吃了,”娘拉起白起,拍了拍他身上的土,土屑掉在地上,“你王爷爷今天肯定也在煮粟粥,冬至嘛,都要吃粟粥。你去了,说不定还能喝上一碗他煮的粟粥,你王奶奶煮的粟粥,比娘煮的香,还放了点红枣,甜丝丝的。”
白起笑着点点头,跟着娘走进屋。屋里的灶间飘着粟粥的香气,还混着点肉干的味道,很暖和。爹正在摆祭品,祭品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桌子是槐木做的,上面铺着一块粗布,祭品摆得很整齐,粟米放在中间,麦饼放在两边,肉干放在最前面,是给先祖的。
“白起,过来祭祖,”爹说,手里拿着三根香,点燃了,递给白起,“给先祖磕个头,保佑你将来从军顺利,立军功,平平安安地回来,让咱白家抬起头来。”
白起接过香,走到桌子前,对着先祖的牌位磕了三个头,头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声,他心里想着:先祖,我将来一定从军立军功,让白家抬起头来,不辜负您的保佑,不辜负爹和娘的期望,做一个让白家骄傲的人。
磕完头,白起坐在灶间的凳子上,拿起陶碗,喝了一口粟粥,粟粥的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很舒服,还带着点肉干的味道,是娘特意放的。娘坐在旁边,看着他吃,脸上带着笑:“慢点吃,别噎着,锅里还有很多,不够再盛。”
吃完粟粥,白起拿起几块麦饼,用粗布包好,就往王有家里跑。王有家在村北,离白起家不远,走一会儿就到了,路上的雪还没化,是昨天晚上下的,薄薄的一层,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响。
王有正在院里晒太阳,手里拿着个陶碗,碗里盛着粟粥,还冒着热气,王奶奶坐在旁边,缝着布衫,布衫是给王有做的,灰色的,很厚实,适合冬天穿。“王爷爷,王奶奶!”白起跑进院,手里的麦饼递过去,“我娘让我给您送点麦饼,刚烙的,热乎,还放了点糖,甜丝丝的,您尝尝。”
王有笑着接过麦饼,放在腿上,拍了拍白起的肩:“你这娃,真是有心,冬至还想着给爷爷送麦饼。是不是又在推演什伍制,遇到难题了?你娘刚才来送祭品,跟我说了,说你为了什伍的距离,饭都没好好吃。”
“您咋知道?”白起惊讶地问,眼睛瞪得溜圆,“娘跟您说了?我还以为娘不会跟您说呢,怕您笑话我笨。”
“你娘也是为了你好,想让我帮你想想办法,”王有说,把陶碗放在旁边的石桌上,“来,坐这儿,跟爷爷说说,遇到啥难题了?是不是什伍的距离不好定?”
白起坐在王有旁边,把刚才摆阵的难题说了一遍:“两个伍的距离,太远了怕中间被冲,太近了怕侧翼被攻,我咋摆都不对,不管怎么挪,都觉得有问题,好像敌兵总能找到突破口,冲进来。王爷爷,您当年在河西,是怎么定什伍距离的?是不是有啥规矩?”
王有拿起地上的两根木枝,摆成两个小圈,代表两个伍,木圈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两尺:“白起,你看,这两个伍的距离,不是固定的,要根据敌兵的兵器来定,敌兵用啥兵器,就定啥距离。魏兵的剑长,能劈两尺远,那两个伍的距离,就要比两尺远一点,差不多两尺半,这样魏兵劈不到左边的伍,也劈不到右边的伍,只能被咱的长戟刺;要是韩兵的箭能射五尺远,那两个伍的距离,就要比五尺近一点,差不多四尺半,这样箭手能互相掩护,射退韩兵,不让韩兵的箭射到咱的士兵。”
白起盯着木枝,突然明白了,像打开了心结:“我知道了!距离不是固定的,要看敌兵用啥兵器,敌兵的兵器长,距离就远;敌兵的兵器短,距离就近,这样才能挡住敌兵,不让敌兵冲进来。我刚才没考虑敌兵的兵器,就随便摆,所以才摆不好,谢谢您啊王爷爷,您一讲,我就懂了。”
“没错!”王有笑着说,摸了摸白起的头,“这就是‘料敌合变’,战场上的情况不一样,敌兵的兵器不一样,什伍的距离、阵形都要变,不能死搬硬套,不能不管敌兵用啥,都用一样的距离,那样肯定会输。当年河西之战,魏兵用长剑,咱的什伍距离就远;后来打韩兵,韩兵用弓箭,咱的什伍距离就近,这样才能打赢,才能立军功。”
王奶奶缝完布衫,把布衫放在腿上,走过来,递给白起一块糖:“白起,别光说话,吃块糖,甜丝丝的,是你王爷爷昨天赶集给你买的,知道你爱吃糖,特意给你留的。你王爷爷当年在战场上,就是靠‘料敌合变’,才活下来的,才立了军功,你要好好学,将来也能活下来,立军功,让你爹娘骄傲。”
白起接过糖,放在嘴里,糖的甜味在嘴里散开,甜丝丝的,心里也甜甜的:“谢谢王奶奶,我会好好学的。王爷爷,那要是敌兵又有长剑,又有弓箭,咋办?又要防长剑,又要防弓箭,距离咋定?是不是很难?”
“那就分层次,”王有说,拿起更多的木枝,摆成三层,“前面的伍举盾,挡弓箭,不让敌兵的箭射到后面的人;中间的伍举戟,防长剑,要是敌兵冲过来,就用长戟刺敌兵;后面的伍射箭,射敌兵,远程攻击,不让敌兵靠近。这样不管敌兵用啥,都能应对,既能挡弓箭,又能防长剑,敌兵冲不过来,还会被射死、刺死,只能投降。你看,就像你练剑,既要会劈,也要会刺,还要会挡,不能只会一样,只会一样,遇到厉害的敌兵,就打不过了。”
白起拿起木片,在地上摆了个三层阵,前面的木片画着“盾”,中间的画着“戟”,后面的画着“箭”,摆得很整齐:“前面伍举盾,中间伍举戟,后面伍射箭,这样是不是就好了?不管敌兵用长剑还是弓箭,都能挡住,都能攻击?”
“好是好,还要练熟,”王有说,“演武场的士兵,每天都练变阵,所以变起来快,不慌乱。你现在用木片推演,将来从军了,就要跟同伍的人一起练,天天练,练熟了,到了战场,才能不用想就变阵,才能挡住敌兵,才能打赢。当年我在河西,每天都跟同伍的人一起练变阵,练了一个月,才练熟,到了战场上,才能很快变阵,挡住魏兵。”
太阳渐渐西沉,冬至的天暗得快,院角的雪开始反光,像撒了层银粉。白起要回家了,王有把那两根木枝递给她:“这个你拿着,想不明白的时候,就用木枝摆摆,比用木片方便。记住,不管是练剑还是学阵,都要用心,不能偷懒,偷懒就学不会,学不会到了战场就会死人,就会输仗,就立不了军功。”
白起接过木枝,小心地放进怀里,对着王有和王奶奶躬身:“谢谢王爷爷,谢谢王奶奶,我明天还来学,还来跟您请教什伍制和变阵。”
走在回家的路上,白起手里的木枝攥得很紧,木枝的凉意透过掌心传来,却挡不住心里的暖。他觉得,今天学到的“料敌合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比练一个月剑还有用。他知道,离他从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要抓紧时间,把什伍制学透,把阵形练熟,将来在战场上,做一名最厉害的秦军士兵,立最大的军功,让爹娘骄傲,让王爷爷和王奶奶骄傲,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骄傲。
第五节:寒夜砺剑盼从军
秦武王元年(前311年)1月15日,大寒,秦国郿邑(今陕西眉县)白家村东头粟田旁。
大寒的风从陇山那边刮过来,带着刺骨的冷,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疼得厉害。风卷着地上的雪沫,打在白起的短褐上,发出“沙沙”的声,短褐已经被风吹透了,却挡不住白起练剑的热情。他站在东头的粟田旁,粟田的麦子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被风吹得有些硬,冻得结了冰,踩在上面很滑。
白起手里握着一把木剑,剑是周师傅新给他做的,比以前的沉,也更结实,剑身上还刻着个“白”字,是周师傅用小刀刻的,笔画很深,很清晰——周师傅说,这是给他的“出师剑”,要是能把这把剑练熟,将来从军,就能当伍长,就能带同伍的人打仗,立军功。
白起穿着厚厚的短褐,短褐是娘用粗布做的,里面絮了点羊毛,很暖和,却还是觉得冷,手指冻得有些僵,握剑的手都有些抖,却没停下练剑——他今年二十岁了,按秦军的制度,明年就要傅籍从军,他要在从军前,把剑练得更熟,把阵形学得更透,这样才能在战场上立军功,不拖同伍的后腿,才能让爹娘骄傲。
“劈!刺!挡!”白起嘴里喊着剑招,声音有些沙哑,是被风吹的,木剑在手里挥舞着,劈向旁边的树干——树干是粟树,不粗,却很结实,树皮粗糙,木剑劈在上面,发出“嘭”的闷响,震得他的手臂有些麻,却觉得很踏实,很有力量。
周师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根竹条,竹条上沾了点雪沫,他看着白起的剑招,时不时指点一下:“劈的时候,手腕再转一点,能更省力,还能劈断敌兵的兵器;刺的时候,腰再送一点,能刺得更深,刺中敌兵的要害,让敌兵失去战斗力。你看,当年我在河西,就是用这招,刺中了魏兵的喉咙,才斩首一级,立了军功,赏了钱和布。”
白起调整姿势,沉下肩膀,手腕转了转,再一次劈向树干,木剑的落点很准,刚好在树干的中间,比刚才更省力了,震得手臂也不那么麻了:“周师傅,我这样是不是就对了?将来从军,用铜剑,也能这样劈吗?铜剑比木剑沉,会不会劈不动敌兵的盾?”
“对了,这样就对了,”周师傅点点头,眼里露出点赞许,“铜剑比木剑沉,却更锋利,只要你现在把力气练够,把姿势练对,将来用铜剑,肯定比现在更厉害,别说劈敌兵的盾,就是劈敌兵的剑,也能劈断。当年我练剑的时候,比你还苦,冬天在雪地里练,手冻得肿起来,像个馒头,也没停,不然哪能在河西立军功,哪能活着回来见我娘?”
白起看着周师傅的手,手上满是老茧,还有一道疤痕,是当年练剑时被木剑划伤的,疤痕泛着淡粉色,很明显:“周师傅,您当年从军,怕不怕?我娘说,打仗会死人,她有点担心我,怕我不能活着回来,怕我像村里的李叔一样,死在战场上,再也见不到她。”
周师傅的脸沉了下来,眼神也变得严肃,却又很快软下来,语气也温和了:“怕,咋不怕?谁不怕死?谁不想活着回家见爹娘?可咱秦人,男丁从军,是本分,是责任,要是没人当兵,魏兵、韩兵就会打过来,抢咱的粟米,烧咱的房子,你娘的粟粥,你也吃不上,你也见不到你娘了。我当年从军,我娘也担心,偷偷哭了好几回,可她还是给我缝了新短褐,让我好好打仗,立军功,活着回来。”
“我娘也会给我缝新短褐的,”白起说,眼里带着点期待,“我娘说,要是我立了军功,她就给我缝件蓝色的短褐,比现在的好看,还絮更多的羊毛,冬天穿更暖和。我娘还说,要是我能赏田,就把家里的粟田扩大,种更多的粟米,将来就能不用再种别人的田,不用再交租了。”
“好样的,有志向!”周师傅拍了拍白起的肩,手掌的老茧蹭着白起的短褐,“你娘肯定会给你缝的,你这么努力,肯定能立军功,能赏田,能让你娘过上好日子。不过你要记住,从军不是为了新短褐,不是为了赏田,是为了保护家里人,为了大秦,为了让咱秦人能安稳地种粟米,吃粟粥,不用怕魏兵、韩兵的欺负。只有大秦强了,咱才能安稳地过日子,才能活着回家见爹娘。”
正说着,远处传来脚步声,是王有,他拄着拐杖,拐杖敲在雪地上,发出“笃笃”的声,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装着草药,是给白起和周师傅的,怕他们冻着:“周师傅,白起,天这么冷,还在练剑?小心冻着,我给你们带了点草药,煮水喝,能驱寒,还能治咳嗽,冬天喝最好了。”
王有走到白起旁边,伸出手,摸了摸白起的手,冻得冰凉,像块冰:“白起,别练了,先喝碗草药水,暖和暖和,冻坏了可不行。你明年就要从军了,现在要好好保护身体,别冻坏了,不然到了军营,练不了兵,还得被军吏罚,说不定还会影响从军,立不了军功。”
白起点点头,跟着周师傅和王有回家。王有家的灶间很暖和,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光照在墙上,晃来晃去。王奶奶正在煮草药水,锅里飘着草药的味道,有点苦,却很暖,还放了点红糖,中和一下苦味。
王有从里屋拿出一块木牍,木牍是杨木做的,很轻,上面用秦篆写着秦军的军功爵制,字迹是王有自己写的,有些地方歪歪扭扭,却很清晰,他把木牍递给白起:“白起,你明年就要傅籍了,这个你拿着,上面写着军功爵的等级,斩首多少能获啥爵,赏啥东西,你看看,心里有个数,将来从军,就知道该怎么立军功,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白起接过木牍,小心地拿在手里,木牍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很暖和。他看着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地认,有的字不认识,王有就在旁边教他:“公士爵,斩首一级,赏钱五千,布二匹;上造爵,斩首二级,赏钱一万,布四匹,田一顷;簪袅爵,斩首三级,赏钱一万五千,布六匹,田二顷,还有仆人……”
“没错,”王有说,坐在旁边,看着白起认木牍上的字,“你要是能获上造爵,就能赏田一顷,比我当年还厉害,我当年只获了公士爵,赏了两亩田,你比我强多了。到时候,你娘就能种更多的粟米,不用再织布到半夜,不用再交租,就能过上好日子。”
白起握紧木牍,木牍的边缘硌着掌心,却觉得很有力量,心里充满了干劲:“王爷爷,我将来一定要获上造爵,赏田一顷,给我娘种粟米,让她不用再辛苦,让她能好好休息,不用再为了粟米和布发愁。”
草药水煮好了,王奶奶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碗里飘着红糖的甜味,喝在嘴里,有点苦,却很暖,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身上的寒气都散了。周师傅喝了一碗,放下陶碗,说:“白起,你明天来武师院,我给你看我的旧铜剑,就是当年在河西用的那把,剑上还有魏兵的血锈,你看看铜剑的样子,将来从军,也能知道铜剑咋用,咋保养,别到了军营,连剑都不会用,让人笑话。”
“真的吗?太好了!”白起高兴地跳了起来,眼睛发亮,“我早就想看看您的铜剑了,您说过,那把剑斩过魏兵,很厉害,能立军功,我明天一定早点去,早点看铜剑。”
天渐渐黑了,外面的风更冷了,吹在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像鬼哭一样。白起要回家了,王有把草药包递给她:“这个你拿着,让你娘煮水给你喝,每天喝一碗,别冻着,别感冒了。明年你从军,我和周师傅会去送你的,给你加油,祝你立军功,早日回来见你爹娘。”
白起接过草药包,小心地放进怀里,对着王有和王奶奶躬身:“谢谢王爷爷,谢谢王奶奶,我明天还来,还来看铜剑,还来学本事。”
走在回家的路上,风还是很冷,却吹不散白起心里的暖。他手里握着木牍,怀里揣着草药包,心里想着明年的从军,想着铜剑,想着军功爵,想着蓝色的新短褐,想着赏来的一顷田。他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在军营里了,可能已经开始练阵,可能已经离立军功不远了,可能已经能让爹娘为他骄傲了。
回到家,娘正在灶间等他,手里拿着件蓝色的短褐,是刚缝好的,还没拆线:“白起,回来了?快暖暖,外面冷吧?你看,娘给你缝的新短褐,蓝色的,你喜欢的颜色,里面絮了很多羊毛,冬天穿很暖和,明年从军的时候,就能穿了。”
白起走过去,摸了摸短褐,布料很厚实,羊毛很软,心里暖暖的:“谢谢娘,真好看,我很喜欢。娘,王爷爷给了我一块木牍,上面写着军功爵制,我将来要获上造爵,赏田一顷,给您种粟米,让您不用再辛苦。”
娘接过木牍,小心地放在木案上,摸了摸白起的头,眼里带着点欣慰和期待:“好,娘等着,娘相信你,你这么努力,肯定能做到。娘现在就给你缝新短褐,缝得厚实点,让你在军营里不冷,能好好练本事,好好立军功。”
白起坐在灶间,帮娘烧火,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暖暖的。他看着娘的手,正在穿针引线,手背上满是老茧,却很灵活,针脚缝得很细,很整齐。他心里暗暗发誓:明年从军,一定要好好打仗,立军功,获上造爵,赏田一顷,让娘不用再辛苦,让爹不用再劈柴到半夜,让白家村的人,都知道他白起,是个厉害的秦军士兵,是个能让白家骄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