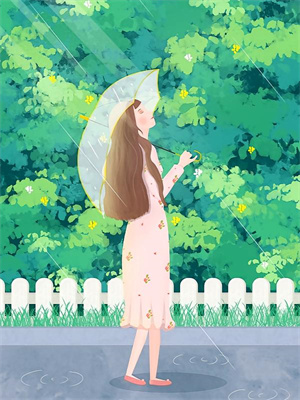简介
《在时间的灰烬里回收记忆》是“三千是只猫”的又一力作,本书以凌辉为主角,展开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科幻末世故事。目前已更新172712字,喜欢这类小说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在时间的灰烬里回收记忆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凌辉踏出车厢的瞬间,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无形的“时间风暴”。
这并非物理意义上的风,而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足以撕裂心智的现实冲击。深时域中央车站的宏伟超乎想象,它并非如地表城市那般向着天空伸展自己的骄傲,而是像一个巨大、复杂、倒置的蜂巢,无尽地向着地壳深处延伸。视野所及之处,并非开阔的广场,而是由无数条半透明的、闪烁着蓝色或白色光晕的磁力管道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这些管道纵横交错,盘旋缠绕,在巨大的地下空腔中形成了一幅令人头晕目眩的动态织锦。
数以万计的、如同幽灵般的居民在这些管道中以惊人的速度移动。他们的个人胶囊车快得几乎要拖出肉眼可见的残影,像穿梭在血管中的血细胞。而在车站的步行平台上,人们的动作同样快得不可思议。在凌辉尚未完全校准的视觉里,他们就像是播放器里被按下了八倍速快进的影像,行走如风,转身急促,交谈的声音被时间压缩得尖锐而短促,失去了人类语言应有的韵律和温度,汇聚成一片高效到令人窒息的、永不停歇的嗡鸣声。
这便是时间流速差带来的“体感压力”。在这里,每一秒都蕴含着标准世界一百秒的信息量。一个未经特殊训练的普通人,其大脑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因为无法处理这爆炸性的信息输入而强制宕机,陷入一种名为“信息休克”的深度昏迷。
凌辉的身体,作为为应对各种极端环境而被深度改造过的“长生锚”,自动开始进行调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胸腔内的那颗心脏,在生物芯片的控制下,开始以一种非自然的、擂鼓般的频率疯狂跳动,将富含氧气和纳米机器人的血液泵向全身。他的神经信号传递速率也被提升到极限,视网膜的刷新率、耳蜗对音频的解析能力、皮肤对环境温度和气压的感知……一切都在超频运转,以此来强行匹配这个疯狂世界的节奏。
即便如此,他依然能感觉到一种微妙的、令人作呕的“延迟感”。就像自己的灵魂被无形的力量拖拽着,永远落后于身体半步。他看到一个行人从身边走过,但听到脚步声时,那人已经出去了五米远。他试图聚焦于远处一块全息广告牌上的文字,但当他看清一个词的瞬间,那个词已经切换了。这种感觉,当地人称之为“时差疲劳”(Chrono-Lag),是所有深时域居民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诅咒,一种永恒的精神与肉体失调。
凌辉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此地“稠密”的空气,强行压下那股想要呕吐的冲动。他静立了足足十五秒,在内心默念着早已烂熟于心的“锚点口令”,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校准技术。当他再次睁开眼时,世界虽然依旧快得疯狂,但至少已经从一盘流动的抽象画,变回了可以被理解的、清晰的影像。
他的任务界面上,代表方舟最后已知位置的标记,正闪烁在深时域地图的边缘地带——第三实验区。那是一个巨大的、以数据处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为主的区域。但同时,凌辉也注意到了在那片高亮区域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在地图上呈现出诡异的暗红色的信号盲区。
那是被官方废弃了超过七十个地表年的“静默档案馆”,一个因为储存了大量“前灵网时代”的、具有潜在污染性的未格式化数据,而被彻底物理隔绝,连城市主脑“万相”都已经放弃了日常监控的地方。
凌辉几乎没有花费任何思考时间,便百分之百地确定了方舟的真正藏身之处。
第三实验区的位置标记,只是一个烟雾弹。方舟比任何人都清楚“万相”的天罗地网。只有那种被时间遗忘、被系统抛弃的黑暗角落,才能躲过那只无处不在的眼睛,进行他那惊世骇俗的“考古”工作。
他不再停留,熟练地走到交通系统旁,登上一辆自动驾驶的、个人专用的管状胶囊车。在身份验证处,他“长生锚”的权限让他无需排队。
“目的地。”胶囊车内响起柔和但毫无感情的AI语音。
“第三实验区,K-11出口。”凌辉报出了一个位于“静默区”边缘的、最冷僻的站点。
胶囊车无声地滑入磁力管道,瞬间的加速度将他轻轻按在座椅上。窗外的城市景观彻底化作了流光溢彩的抽象线条。凌辉看着那些在光线中一闪而过的、巨大而单调的建筑群轮廓——它们是看不到窗户的实验室,是没有娱乐设施的数据中心,是如同蜂巢般排列整齐的个人休眠仓。这里是这座城市赖以运转的无数器官,却没有一丝一毫为“生活”而设计的痕迹。
这里的一切,都只为“效率”而存在。包括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又回到了那个阳光和煦、时间缓慢的过去。
那是在首都大学的露天咖啡馆,他和方舟最喜欢待的地方。午后的阳光是真实的,温暖地洒在身上,能闻到空气中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方舟不喜欢加糖的咖啡,他说苦涩能让人保持清醒。他总是那么激动地挥舞着手臂,仿佛要将自己内心奔腾的思考全部展示给凌辉看,向他描绘着一个他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冷酷的未来。
“他们会建造一座时间的牢笼,辉!你信不信?”方舟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那股穿透力却让周围几个正在谈笑风生的学生都下意识地安静了下来,“他们会告诉全世界,为了加速人类文明的进程,为了更快地攻克癌症、研发出曲率引擎,我们需要一批‘先行者’。他们会把一群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头脑,我们之中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全都关进一个时间流速快一百倍的地方,让他们用一百倍的速度去思考,去实验,去消耗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这些活在标准时间里的‘普通人’换取科技的进步。”
他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眼神里是凌辉从未见过的悲哀。
“这和把小白鼠送进实验室,观察它们如何衰老、病变,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这更残忍!因为那些科学家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亲手将自己生命的进度条,调成了快进模式。一年之后,当他拖着一颗运转了一百年的、疲惫不堪的心智,走出那座牢笼时,他会发现,他所研究的一切或许早已改变了世界,但他所熟悉的世界,却早已不再属于他。他的亲人、朋友、爱人,在他感觉中的‘一年’里,已经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生老病死。他将变成一个活着的、与自己创造出的时代彻底脱节的幽灵。”
凌辉靠在胶囊车冰冷的金属内壁上,缓缓闭上了眼睛。他仿佛还能感受到那个下午的阳光温度,还能闻到那杯黑咖啡的焦香。
方舟啊方舟,你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透彻,那么精准,仿佛亲眼所见。却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走进这座你亲口预言的牢笼,变成一个与整个时代为敌的幽灵。你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吗?还是为了……寻找一个拯救所有人的方法?
就在这时,在他那被严密逻辑和精神训练守护的意识深处,那个被他强行封存的、属于LT-73的记忆碎片,突然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却尖锐如针刺的冰冷悸动。
“……他……在说谎……”
那声音不再是一段被动存储的信息,它像一个有了自主意识的活物,在他的脑海中低语。这股外来的意念,似乎是被他此刻因回忆方舟而激荡起伏的情绪所引动,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一种混杂着极致的愤怒与不甘的情绪,像一缕黑色的寒气,试图从那个被他封锁的记忆区域中渗透出来。
凌辉的眉心猛地一蹙,一阵尖锐的刺痛从大脑皮层传来。他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低估了这段记忆碎片的“活性”。它不仅仅是一段遗言,它是一个被污染的、充满攻击性的“精神模因”。
他立刻调动起作为“长生锚”的专属权能,将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集中起来,像一层坚韧的屏障,重新将那片躁动的记忆区域包裹、加固、上锁。这是一个极其耗费心神的精细操作,他的太阳穴上渗出了一丝细密的、冰冷的汗珠。
当那股悸动终于被重新压制下去时,凌辉才缓缓松了一口气。他意识到,自己携带的这枚“证据”,远比他想象的要危险。它是一颗随时可能在自己脑中引爆的、逻辑与情感混合的炸弹。他必须在处理完方舟的事情后,尽快找到破解它秘密的方法,否则,他自己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记忆熵增已达临界红线”的回收目标。
胶囊车在此时缓缓减速,停靠在了K-11出口。
“前方为一级管制‘静默区’,未经四级以上权限许可,禁止进入。祝您愉快。”AI的提示音依旧冰冷而单调,仿佛在播报天气。
凌辉走出车站,一股与深时域那高效、洁净的主城区截然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面前是一道高耸入顶的、锈迹斑斑的合金隔离网,上面挂着的全息警示牌因为能源供应不足和年代久远,正闪烁不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与背后那个光鲜亮丽、高效运转的第三实验区相比,这里仿佛是城市肌体上一块正在腐烂的伤疤。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封已久的、难以名状的怪异气味。那是金属在百年尺度上缓慢锈蚀的味道,是早期化学品在容器中挥发、变质的味道,更是灰尘的味道——一种被时间研磨得无比细腻的、万物的残骸。
他没有走正门,那里的警报系统虽然老旧,但仍有可能将他的行踪上传给“万相”。他沿着隔离网行走,凭借“长生锚”对能量流动的敏锐感知,他轻易地找到了隔离网的一处供能线路的薄弱点。他从风衣内侧取出一个小巧的电磁脉冲装置,对着那里轻轻一按。一圈无形的波纹散开,隔离网上的电流瞬间中断了三秒。
足够了。
他如狸猫般,悄无声息地闪身而入。
进入“静幕区”的瞬间,仿佛从一个喧嚣的世界,一步踏入了坟墓。
这里,时间的绝对破坏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百倍的流速,意味着这里的一年,在宏观尺度上,就相当于地表世界的一个世纪。那些曾经代表着人类最尖端科技的建筑,如今都已在外墙上布满了风化和剥落的痕迹,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在无声地诉说着被遗忘的痛苦。街道上,被遗弃的车辆和实验设备,像远古巨兽的骸骨,静静地躺在那里,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仿佛灰色积雪般的灰尘。
这里安静得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血液在血管中流淌的微弱声响。与外面那个喧嚣、急促的世界,判若两地。
凌辉半蹲下来,摘掉手套,用手指捻起一点地上的灰尘。在指尖轻轻揉搓,他能从中分辨出极其微弱的、不属于这里的能量粒子残留。那是方舟的反重力背包在低空掠过时,排出的推进介质留下的痕迹。非常微弱,换做任何电子仪器来,都会将其当做背景辐射忽略掉。但他的“锚”之权能,让他对任何时间的异常流动和能量扰动都极为敏感。而方舟这样一个“活物”,在这样一个死寂了近百年(地表时间)的地方,就像黑夜中的一根火炬一样醒目。
他站起身,不再有丝毫犹豫,顺着那几乎无法被凡人察觉的痕迹,向着“静默区”的最深处走去。
沿途,他看到了更多方舟留下的、令人心惊的线索:
在一个废弃的岗亭里,他发现了一个被捏得严重变形的、早已过期的营养膏空管。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换算成地表时间,是十五年前。这意味着,方舟在这里,至少已经孤独地坚持了十五个地表年。
在一堵倒塌的墙壁上,他看到了一块被丢弃的、屏幕已经碎裂的便携数据板。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用记号笔写下的、潦草而狂乱的复杂公式和逻辑推演,旁边还有一句用通用语写下的话:“他们藏起来的,不是技术,是历史。”
在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他发现了一小滩已经凝固的、颜色发黑的血迹。他蹲下身,用指尖沾了一点,放到鼻尖轻嗅。是鼻血。以他的专业知识判断,这是因为长时间进行高强度的精神链接,导致大脑超负荷运转,毛细血管破裂所致。
凌辉的心,随着发现的线索越来越多,一点点地往下沉。他能清晰地想象得到,自己的这位老友,是在怎样一种燃烧生命、透支精神的疯狂状态下,进行着他最后的、孤独的抗争。他不是在搞研究,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凿子,试图凿开这个时代最坚硬的基石。
最终,他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深埋于地下的圆柱形建筑的入口处。根据旧时代的地图记载,这里曾是整个第三实验区的“能量井”,为所有的实验提供动力。一股微弱的、由老式核能电池衰变时发出的特有嗡鸣声,正从深不见底的井底传来。
那里,就是方舟的藏身之处。
他找到了紧急维修通道的入口,顺着盘旋向下的、布满铁锈的楼梯,一层一层地向下。越是深入,空气中的信息干扰就越是强烈。那是一种无形的、混乱的“噪音”,是方舟为了破解“万相”的防火墙而制造出的“逻辑干扰场”,足以让任何试图通过电子设备追踪他的敌人瞬间失灵。
但这对于只依靠最原始的直觉和“锚”之感应的凌辉来说,这反而像一座在迷雾中闪烁的灯塔,为他精准地指明了方向。
他最终停在了地下约三百米深处的一扇门前。
那是一扇厚重得如同金库大门的、由铅和陶瓷复合材料制成的圆形舱门。这种门是“前灵网时代”用来隔绝最高级别辐射和信息泄露的。门上没有任何电子锁,只有一个古老的、因为常年使用而磨损得油光发亮的黄铜锁孔。这是整个“静默区”里,唯一一个理论上能百分之百隔绝“万相”监控的地方。
凌辉能清晰地“感觉”到,门后,方舟那极度亢奋、同时也极度虚弱的精神波动,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剧烈地摇曳。
他成功了。但也快要油尽灯枯了。
现在,任务流程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只需要一脚踹开这扇并不牢固的门,或者用脉冲枪熔开它。然后,用手中的“静默”,对准他的额头,按下开关。
任务,便能完成。他可以回到浅时城,回到自己那个安静的书房,假装这一切从未发生。
凌辉站在门前,从风衣内袋里,缓缓取出了那支冰冷的、笔状的银色金属工具。他紧紧地握在手中,那熟悉的、代表着绝对权力的触感,此刻却有些烫手。
他看着厚重的舱门上,自己那张被锈迹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模糊的倒影。那张脸冷峻、漠然,眼神里是“长生锚”特有的、被剥离了情感的空洞。他有一瞬间的恍惚。
照片里那个在咖啡馆里与朋友争论得面红耳赤的理想主义青年,和眼前这个双手即将沾满故友鲜血的冷酷刽子手,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忒修斯之船……”他无声地动了动嘴唇。
他深吸了一口充满了铁锈和臭氧味道的空气,强行压下了心中那片翻涌如海啸的情绪。
但他没有选择用暴力破门。这个选择,甚至没有经过他的大脑思考,而是身体的本能。
他抬起右手,用指关节,在那扇冰冷的金属舱门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敲了三下。
咚。
停顿了半秒。
咚咚。
一声长,两声短。
这是他们学生时代,去对方宿舍时约定的暗号。那个时候,他们都喜欢在学习时戴上降噪耳机,只有这个独特的节奏,才能让他们在不打扰对方思路的情况下,知道是朋友来了。
一个被遗忘了近一个世纪的、毫无意义的、属于过去的暗号。
门后的嗡鸣声,戛然而止。
方舟那原本如同风暴般狂乱的精神波动,也瞬间平息了下来。
死一般的寂静中,一个沙哑、疲惫,却带着一丝了然笑意的声音,从门后清晰地传了出来。
“我就知道,他们会派你来,凌辉。”
短暂的停顿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仿佛等待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复杂情绪。
“你是来见证真相的,还是来……抹除真相的?”